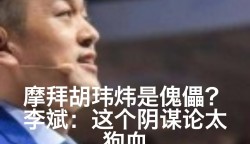一方面,蚂蚁金服拥有当前市场上较为全面且稀缺的金融牌照,包括网商银行、天弘基金、支付宝(第三方支付)、小贷、保险等,蚂蚁金服还出现在近期曝光的五家金控监管试点名单中;另一方面,蚂蚁金服更强调自身是技术公司,要做的是TechFin(用技术服务金融机构),与外部许多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在其员工团队中,技术人员的比重很高。
在刚刚过去的五月,蚂蚁金服密集宣布了多项对外开放进展:先后牵手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和浦发银行,余额宝接入多家基金公司,花呗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放。结合当前金融严监管态势,市场不乏有疑问声音:这是否是蚂蚁金服应对监管压力做出的战略调整?
“我们从没想过要做一家金融机构,目标就是要做一家科技公司。”蚂蚁金服副总裁陈亮称,当初注册商标“蚂蚁金服”,重在“服”而不是“金”。但市场显然对蚂蚁的“金”给予了更高的关注度。“五年前要是能判断今天的局面,就不会在蚂蚁金服的工商注册名里放一个‘金’字。”陈亮打趣道。
亦有市场声音指出,目前蚂蚁金服自营金融业务占比还较高,消费金融业务是利润的主要贡献。在开放时间上也相对较晚,对外开放力度还不够。
无论如何,当前蚂蚁金服对外部机构开放的节奏在加快,蚂蚁金服能否扭转其在外界眼中的“金融机构”人设?
金融业务“试验田”
蚂蚁金服最初是以传统金融的挑战者姿态入局。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的一句“银行不改变,那我们就来改变银行”时常被引用。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造成了错觉,好像我们要变成一个金融机构的角色,其实从来没有。”陈亮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们希望通过技术的变革和发展,去推动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变革。”
资料显示,蚂蚁金服在2015年提出互联网推进器计划,称要在5年内通过技术帮助1000家金融机构。外界更熟知的是,蚂蚁金服在2017年3月明确提出要做TechFin,未来“蚂蚁金服只做Tech(技术),支持金融机构去做好Fin(金融)”。此后,蚂蚁金服的对外合作较多落地,在今年5月达到一个开放的小高潮。其间,蚂蚁金服的对外开放似乎出现了断档。
反观同时期的京东金融,在2015年就反复提出“不与金融机构抢生意,而是用技术服务金融机构”。京东金融与金融机构合作也从2015年开始,在2016年和2017年均有大量合作案例。
“我们不能拿金融机构当做小白鼠,只能自己当小白鼠,这意味着要有一些自有场景试验田去锤炼技术,服务好了才有资格、胆量去服务外部机构。金融又是强监管领域,必须得拿牌照接受监管,但不代表蚂蚁要做一家金融机构,我们内部也没有把牌照作为稀缺资源。”陈亮称。
无论是蚂蚁金服还是京东金融,都表示在业务开展之初就尝试过寻找金融机构合作,但要么被金融机构拒之门外,要么合作进展极其不顺利。
蚂蚁金服副总裁、网商银行行长黄浩曾任建设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于2016年初加入蚂蚁金服。黄浩介绍,阿里小贷最初就是要和建设银行合作为小微企业解决信贷难题,但当时双方的风控和理念完全不同,阿里推荐给建行的贷款客户百分之七八十都被否决了。
媒体曾报道,余额宝最初也曾想与大型基金公司合作,但没有公司答应,最后选择合作的天弘基金当时连年亏损全行业垫底。支付宝最初希望在银联开辟支付通道,但遭到拒绝。
今非昔比,如今支付宝全球活动用户达8.7亿,超过“宇宙行”工行个人客户数;余额宝规模达到1.58万亿,带动天弘基金成为行业第一。蚂蚁金服方面称,业务模式上“成熟一个开放一个”。
黄浩表示,“当初的支付宝和阿里小贷都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怎么让金融机构相信你?需要探索出有效的模式并经过时间的检验,阿里小贷走过八年,现在服务到近千万家小微企业,现在才具备开放的条件,再谈开放银行也都愿意合作。”余额宝走过五年开始对外开放,花呗、借呗历时三年。“这个周期在缩短,我们相信未来每一个业务在试验田里的时间都会越来越短。”
黄浩介绍,蚂蚁金服开放合作模式非常多元,包括流量层面、场景层面、客户层面、技术层面、数据层面等。例如主要服务农村客户和小微企业的地方银行桂林银行,将场景开放给蚂蚁金服,蚂蚁金服提供数据和技术服务,使其业务在线化。而如南京银行等,蚂蚁金服则把核心技术全部开放,包括数据运营、内部风控、风控系统开发等。
自营金融验证金融科技能力,再开放赋能给金融机构,这是当前京东金融、蚂蚁金服和百度金融向市场讲述的同一个演变路径。
但对于蚂蚁金服的对外开放,有行业人士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交流时表示并不买账。其认为,蚂蚁金服此前较多着眼于自营金融业务发展,在当前金融严监管的形势下打出开放牌,诚意略有不足。
消费金融服务仍是利润贡献大头
对于金融科技公司,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其营收来源主要是技术服务还是自营金融业务?
根据阿里巴巴披露的财报以及与蚂蚁金服之间的分润协议比例推算,蚂蚁金服2017年的税前利润达131.89亿元。其中第四季度盈利大幅下滑,阿里巴巴解释是支付宝钱包推出的激进的用户增长计划,使得针对新用户的补贴成本大幅上升。2018年第一季度,蚂蚁金服出现亏损,财报称蚂蚁金服继续加大投资,为实现用户的强劲获取和参与。
根据能获得的公开数据,花呗为代表的蚂蚁小微小贷2017年上半年净利润为10.2亿元,借呗为代表的蚂蚁商诚小贷在2017年前三季度净利润44.93亿元。知名金融科技观察自媒体“新金融琅琊榜”审慎估算,称2017年蚂蚁金服消费金融业务净利润有望在80亿元左右,占其净利润比例达六成。
对于上述分析,蚂蚁金服方面并未直接回应,由于蚂蚁金服尚未上市,其具体财务数据暂未可知。
一份流传的融资文件显示,蚂蚁金服2015年时营收六成来自支付接入服务费,两成来自金融服务,另有超过一成来自技术服务。而到2017年,其支付接入费用占比下降至五成,技术服务收入上升至三成,而金融服务缩水至一成。蚂蚁金服并未确认文件的真实性,但接近人士表示,数据比较合理。
一位市场人士分析称,营收结构与利润结构并不相同,因为蚂蚁金服对支付业务进行了大幅补贴,因此支付业务利润贡献有限。蚂蚁金服当前的利润结构中,以花呗、借呗为代表的消费金融业务是利润贡献的大头。
“如果未来技术服务收入不占大头的话,我们哪敢说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接近人士表示。
上述文件还指,到2020年左右,营收中60%将来自技术服务费,30%来自支付接入服务费,来自金融的收入占比将降至10%以下。“这个结构会是比较合理的,也是金融科技公司应有的特征。”
如何监管蚂蚁金服
原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无论是否叫金融科技公司,一旦触及需要持牌的金融业务都需要申请相应的牌照。而对于持有较多金融牌照又称要做金融科技的公司,最起码在第一步的牌照关是合规的。
在蚂蚁金服发展的历程中,推动移动支付领先全球以及补位小微企业信贷等作用和创新之外,一些或明或暗的业务风险愈发被监管部门关注。但这样一个独特的机构,对于监管部门也是新课题。
以小贷ABS杠杆风险最为典型。曾有持牌消费金融公司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特别在发行ABS方面,消费金融公司受到严格的杠杆限制,自持资产占有相当比例。而蚂蚁的相关业务杠杆率则没有明确限制,累计发行规模数千亿,成为利润贡献主力。其自持资产比例较低,一旦发生风险,则可能出现“雪崩”。在2017年末的互联网风险专项整治工作中,小贷以信贷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名义融入的资金应与表内融资合并计算,网络小贷杠杆率窟窿被堵上。
2017年12月,蚂蚁金服宣布对旗下两家小贷公司增资82亿元,将注册资本从现有的38亿元提升至120亿元。后续将视业务开展情况和相关的监管要求,继续增加注册资本和资金实力。
此外,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其庞大规模引发监管对其流动性担忧。2017年起,余额宝不断限额,个人持有额调整至10万元,单日申购额度2万元。此后,余额宝还设置了单日的申购总量,T+0快取额度于6月6日起降至1万元。人民银行和证监会就6月1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中指出,货币基金“T+0赎回提现”容易使投资者忽略货币市场基金自身蕴含的投资风险属性,忽视普通赎回安排,同时,垫支机构也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市场极端情形下易引发流动性风险,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亟需加以规制。
接近监管部门人士还提到,在“侨兴案”事件中,蚂蚁金服由于不在监管部门管辖范围内未承担相应责任。尽管“侨兴案”在广发天价处罚中的责任比重较小,但应关注蚂蚁金服将高风险产品销售给不合格投资人的风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蚂蚁金服在2015年就停掉了所有地方资产交易所的合作,不再销售相关产品,2016年爆发的侨兴债违约属于历史存量业务。
蚂蚁金服方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定位科技公司并不是为了回避监管,“试验田”也同样在监管范围之内。
对于蚂蚁金服来说,其在新业务探索的过程中并未违反现有监管规定,但暴露出一些此前监管并未覆盖或注意的空白领域。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曾建议,对于系统重要性数字金融机构,尝试看有没有办法像传统金融机构那样,进行一些压力测试,对其资本金、流动性、业务范围等做一些特殊监管要求。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多次呼吁,中国金融科技监管要注重微观功能监管与宏观审慎管理结合。微观功能监管采取穿透式监管,按相关业务类别由相关监管当局监管,实现监管全覆盖。在宏观审慎管理中,应当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制定特别监管政策,如额外增加资本金、建立生前遗嘱等。而且很重要的是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科技公司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在外界看来,拥有8.5亿支付用户的蚂蚁金服显然已经是系统重要性机构。